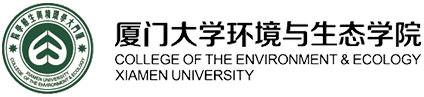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 吕士成/摄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笔下描述了无数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
今天,在钢筋混凝土浇灌起的一座座城市中,鸟声、鸟影日渐稀少。
基于对中国城市鸟类近20年的观察数据,厦门大学讲席教授吕永龙团队及其合作者展示了首个洲际尺度的“快照”:许多受威胁鸟类分布的热点区域与城市化的热点区域高度重合,而且越是种类稀少的鸟类受到的不利影响越大。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城市化,重塑的不只是鸟类多样性版图。吕永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从动植物多样性到人类的社会生态,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始于一场“错位”的对话
吕永龙依然记得,1991年中英两国生态学家的一次“错位”的对话。那时,英国生态学会代表团来华访问,尽管两边的参会者都是城市生态学者,但双方的关注点并不一致。
“英国方面的几个人都是鸟类学家,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的市中心有很多鸟,则说明它的生态是好的;而我们中国做城市生态学研究则是把人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导的生态系统。”吕永龙回忆道。
后来,再反思那场对话,吕永龙越来越觉得,城市作为一个以人为主导的生态系统,必须考虑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几年前,为了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供科学支撑,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科学委员会。当时还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吕永龙就曾提出,应将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为一个前沿方向进行研究。
随着全球城市人口总数不断上升,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影响的前沿研究显得日益重要。但这个领域的研究存在“短板”,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长时间序列的定点观测数据,在宏观尺度下研究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极具挑战。
吕永龙团队想填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空白。但要用哪种生物作为指示物种呢?从地下、地表到空中,最终他们将目光停留在鸟类多样性上。
“鸟类的数据相对比较充足。”吕永龙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数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以及城市鸟类爱好者汇集的观鸟数据,都为了解城市化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支撑。
基于这些多源观测数据,他们收集了2000—2020年大量鸟类活动的观测信息,分别获取鸟类的潜在分布区和实际分布区,并整合不透水面、夜间灯光和土地覆被数据,对城市化影响下鸟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和物种相似性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发现,受威胁鸟类分布的热点区域与城市化热点区域高度重合,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不透水面面积增长最快,这个地区也是受威胁鸟类的热点地区。
这些热点地区也与受夜间照明影响强烈的地区重叠。人造灯光会扰乱鸟类的行为,导致候鸟夜间飞进建筑物。这通常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他们认为,持续的城市化和人类活动的增加日益限制了受威胁鸟类的栖息地范围。
此外,研究发现城市化对广域种和狭域种会产生相反的影响,狭域种受到的不利影响相对更大。这种不对称影响和同质化的城市环境使得区域间鸟类物种组成的相似性更高。
失而复得的鸟类家园
尽管如此,研究团队指出,积极的保护策略仍然可以有效缓解上述不利影响。
辽宁盘锦就见证了鸟类家园的失而复得。作为辽河入海口,这里被誉为“轻轻放在湿地上的城市”,栖息着丹顶鹤、黑嘴鸥等260多种鸟类,一望无际的红海滩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然而,由于围海养殖、过度农业开发、石油开采以及工业发展,从1986年到2000年,盘锦自然湿地减少了700多平方公里,到了2005年在辽河三角洲仅观测到10对丹顶鹤繁殖。
为了发展生态城市,2015年起盘锦“壮士断腕”,启动“退养还湿”工程,拆除一批养殖设施,并将所有石油开采相关设施从辽河口自然保护区迁出。到2020年末,该市恢复了近60平方公里的湿地,以及17.6公里的海岸线。根据《中国沿海水鸟同步调查报告》,当地水鸟物种数量由2005—2011年的94种增加到2012—2019年的112种。
另一个案例是江苏盐城。从“人鸟争食”到“为鸟留食”,从“湿地养鱼”到“退渔还湿”,这些措施让盐城成为“国际湿地城市”。目前盐城条子泥湿地鸟类已达410种。
“这些案例说明,城市化会给生物多样性带来挑战,特别是滨海城市。如果进行适宜的改造和生态修复,也会达到非常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吕永龙说。
不只是在滨海城市,近几年很多内陆城市规划中的绿地空间、水面空间的分布更加均匀。这使得在绿色基础设施和植被覆盖指数更高的城市,如北京和广州,鸟类多样性比周边城市更高。
《科学进展》国际评审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填补了‘南方’地区(即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认知空白,可以为制定2020年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及缓解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提供新的认识。”
城市生态应有“个性”
城市生态重建,不止一种模式。2018—2022年,太原、深圳、徐州等11个城市被列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作为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专家组核心成员,吕永龙经常为示范区的建设出谋划策。在他看来,城市发展速度、历史底蕴、资源禀赋都会影响它的生态发展模式。
“从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必须考虑其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吕永龙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压力和疾病也需要有适度的自然空间来缓冲,这样有助于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太原、徐州则是资源型城市,在进行地面沉降、重金属污染等生态修复的同时,需要着眼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一体化综合治理和修复。
此外,一些古城则需要在“修旧如旧”的同时,增加新的生态要素。
吕永龙告诉《中国科学报》,城市生态修复不仅要考虑人的需求,还要考虑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城市里的植被增加了、水面增加了,鸟类自然就来了,人也会更愿意靠近这样的环境。而国际上很多前沿研究已经发现,城市绿地有助于缓解高强度生活带来的抑郁及各种疾病。”他说。
在吕永龙看来,当前,城市生态建设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还不够”。这与“同质化”的城市生态修复不无关系。以北京为例,大部分绿色基础设施是柳树、梧桐树、银杏树,这势必会影响鸟类和其他生物的多样性。他建议,未来制定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时应更加关注本土物种的多样性。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de3061